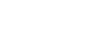来源标题:德国电影,并不一定“德意志”
2023年德国电影展于11月17日在京启动,本次影展在北京德国文化中心·歌德学院(中国)进行,全部放映活动免费面向公众。影展将给大家带来12部影片,其中包括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得主《音乐》、戴锦华老师盛赞的《戏梦空间》、代表着迷影精神的《格雷戈尔夫妇——跟我来电影院吧》、关于现代舞大师皮娜·鲍什的纪录片新作《起舞的皮娜》以及在豆瓣呼声很高的《德黑兰的七个冬天》等。在精彩影片呈现之前,不妨先让我们跟随文章,走近当下的德国电影,去了解它的关切、思考与主张。
《格雷戈尔夫妇——跟我来电影院吧》与德国电影的“全人类”视野
“迷影精神”可以用直观的数字来注释:有一对夫妻,用65年的时光看了10万部以上的电影,正常人大概都不会对这个数字无动于衷。这就是德国电影传奇人物格雷戈尔夫妇。但他们并不仅仅为了打发时光,电影是他们与时代的互动,是思想的表达,是抗争,也是实现人文理想的主要媒介。他们一起创办了“兵工厂”艺术电影院,并在柏林国际电影节设立了“青年电影论坛”单元。这个单元培养了不少优秀的导演。到这个份上,对于这对神仙眷侣来说,电影已经是生活和生命本身,是通往自我理解的途径。纪录片《格雷戈尔夫妇——跟我来电影院吧》堪称一部迷影教科书,也是今年各大电影节展映的热门电影。它也在最近举办的“德国电影展”放映。
之所以首先谈这部纪录片,因为涉及到笔者对德国电影的一个观察,即继上世纪“新德国电影运动”以来,德国电影越来越呈现出一种“全人类”的视野。这意味着想当然地用“国别电影”或“民族电影”去看它是不够的,就像人们常常想当然地以为好莱坞电影具有“国际视野”一样简单化——好莱坞电影反而是更明显的“国别电影”。
格雷戈尔夫妇的行动其实更带有欧洲人文主义知识分子色彩。诚然,德国电影生产了很多“德国故事”,20世纪的历史为此提供了大量资源,特别是“二战”故事和东德“史塔西”故事(以《窃听风暴》为代表),是德国大众电影的基本盘,同时也满足了德国以外观众喜闻乐见的“德意志想象”。但是明眼人不难看出,其中的优秀作品多少都提供了历史反思,尤其是对于民族主义历史的反思(这一点确实比日本电影做得好)。
民族主义真正起源于德国浪漫主义。它尽管有过荣耀,虽然如本雅明列举的德意志知识分子(康德、歌德、荷尔德林等人)体现了真正的人文精神,但毕竟浪漫派影响下的某种思想最后通往了20世纪的人类悲剧。黑格尔所谓“历史性的民族是一往直前的宇宙精神”这种说法在今天的德国是被非常谨慎地看待并理解的。
但是也能看到,德国电影作者的创作对欧洲乃至全人类命运均有较为深度的关切,这来自他们对近几十年德国移民问题(土耳其、叙利亚、希腊等)的目睹与思考(其中不乏优秀的移民后代作者,比如法赫提·阿金),也来自于一种对更严重的人类危机的焦虑。焦虑显然来自于他们的历史经验,因为这种危机一旦爆发就是毁灭性的。但作为艺术家,似乎也只能用艺术来表达这种关切。
《起舞的皮娜》与现代性思考
这次展映中包括好几部优秀纪录片。老将施隆多夫的《造林人》,入选柏林电影节的《德黑兰的七个冬天》,会引发咱们会心一笑的《东德时尚往事》都值得一看。而出生于1984年的弗洛里安·海因森-齐奥布导演的纪录片《起舞的皮娜》亦不容错过——这是继香特尔·阿克曼的《有一天皮娜问我》和维姆·文德斯的《皮娜》之后,又一部关于现代舞大师皮娜·鲍什的纪录片。不同的是,它记录的是皮娜的弟子在皮娜去世后,复排两部经典,即《伊菲吉尼亚》和《春之祭》的过程。前者起用的是著名的德累斯顿芭蕾舞团班底,后者则与来自塞内加尔的非洲民间舞者合作(他们大多数是街舞舞者)。这两种合作情况实际上都很艰难。
笔者认为可以先去理解皮娜·鲍什的重要意义。她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革新了舞蹈的表现形式,比如用表现主义革新了古典舞蹈的语汇;也不仅仅是“自由”,比如显而易见,皮娜的舞者在身高、身材方面都没有古典舞那么苛刻的门槛,这或许让人想到“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这个浅层方向的解读,或许将之理解为一种性灵的自由抒发,理解为随性的、解放身体的自由舞蹈。其实,皮娜舞蹈的技术含量非常高。
最重要的一点是,皮娜是一个思想者、艺术家。不理解这个层面,就难以接触到她作品的灵魂。这意味着,皮娜通过自己的艺术与同时代的思想家进行了同等程度的思考。正是皮娜告诉我们,一个优秀的舞蹈家毫无疑问能够具备深刻的思想性。皮娜的艺术呈现出一种脆弱感,运动规律是下坠的。这与古典芭蕾正相反,古典舞以灵魂的上升为最终旨归,因此无论多么悲伤的剧情,芭蕾都必须给人轻盈感,总要去克服地心引力。而皮娜的创作里没有什么飞升,连这种欲望都显得是虚妄的。她表达沉重,肉身和灵魂同样的沉重,是现代人普遍的精神肖像。她肯定比很多哲学家都更准确地为我们呈现出了这一点。她的创作并非简单的私人的小情小爱死去活来的那种抒情。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身为“现代人”一分子的自己与这些舞者所传递的愤怒、绝望、忧伤、恐惧、苦难、怨恨之间的相关性,因为这些舞者非常“准确”地传递给我们。与此同时,通常还会让我们感受到一个更大的、给人压迫感的社会背景,而且绝非仅仅是一种“德意志故事”。皮娜说,重要的不是怎么去跳,而是为什么跳——仅这一点,就已经足以将那些仅仅把舞蹈理解为“美美的”舞者与观众排除在外。
这部纪录片里排演的《伊菲吉尼亚》和《春之祭》题材都非常残酷,那就是活人献祭,并且这个祭品必须是一个年轻的处女。欧里庇得斯的悲剧和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本身已经是非常强大的艺术存在,但皮娜的舞蹈竟在这两位大师面前毫不逊色。她毫不妥协地向经常被美化的“古老传统”——暴力、复仇、献祭这种“冷酷祭典”中的非人性、残暴、荒淫开战——这不是宿命论,而是反抗的悲剧。仅仅看当代的新一代演员如何在排练中逐渐理解皮娜的思想,也是值得的。而这种人文思想与非洲文化的融合,以及在排练中遭遇疫情而被取消演出的挫败,又为这种精神传递增加了厚重的色彩。
《戏梦空间》的别致与阶级议题
出生于1986年的索菲·林南鲍姆导演的《戏梦空间》去年上映以来就备受关注。其实片名译作《平凡的人们》更妥,“戏梦空间”这个带有剧本杀味道的译法好像把影片理解为一种玩弄技巧的烧脑游戏,从而将影片最重要的核心遮蔽了。
这是一部典型的反乌托邦电影,而且是一部“元电影”,很多地方让人想起茂瑙那部经典的反乌托邦神作《大都会》。索菲显示出新一代导演对各种反乌托邦叙事的熟稔,同时也表明了“反乌托邦”并不仅仅与某段历史或某种意识形态关联,而是将在更长的时间段中发挥它的“现实意义”。
就像“新中世纪”一样,索菲的这个故事建立在既新又旧的时空背景上。这个背景看上去似乎像是“铁幕”时期,间或又有点“第三帝国”的味道。但是,上流阶级的黑白通婚,以及穿着女仆装的男仆,又意味着对当下欧洲现实议题的指涉,即对种族、性别旗号的一种反讽:这些大旗通常并不通往它们预设的目的地,倒时常导致新的不公正。
索菲用电影业的行话建立起一种隐喻:在这里“主角”是最高阶级,“配角”在“主角学院”学习后,有可能成为“主角”。但是“废材”(即被剪辑掉的花絮、跳接、废片等,即“底层”,“普通人”)是不配的——他们不配拥有自己的BGM(主角随时随地都能来一段歌舞),甚至不配拥有色彩,不能拥有自己的“读心器”,更不可能有阶级跨越的通道。
主人公、女孩葆拉是“配角”母亲和“主角”父亲的孩子。她出生就被父亲遗弃,因为她是没有色彩的。但母亲想方设法给她弄到读心器,并给她服用彩色胶片修复药,哄她说是心脏病药物;还谎称她的父亲在大屠杀中遇难,并送她去“主角学院”,以期她能够实现“逆袭”。但偶然中,葆拉对父亲的下落产生了好奇。在寻父之旅中,她终于发现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并进入了“废材”的真实世界:他们是被审查的,被删除的;他们不适宜的话要被消音,被打马赛克;他们的反抗有各种方法被压制。葆拉最后在“主角学院”的考试中证明自己的实力后,勇敢地擦抹掉脸上的色彩,还原了自己的真实身份,拆除了读心器——这引发了现场观众的同情和支援。最后,葆拉一家离开,走向被剪辑掉的、未知的、荒凉的大地(流放地?)。当然,这也是“剧情”。
不得不说,作为一部剧情片,此片给人枝蔓过多、逻辑不清的感觉,甚至有些“虎头蛇尾”。比起一些经典的反乌托邦电影,它也谈不上有什么突破。新媒体时代,处理阶级议题或许比导演想象得要难很多。但我们依然能感觉到新一代导演的关切:作为复数的“普通人”,他们的声音被淹没并非是理所当然的。此外,这部影片似乎还想表达:“话语”塑造了意识形态;话语宣布了“废材”是社会不安定的来源(这样他们就可以背所有黑锅);话语也规定了“上流阶层”应该如何生存(怀疑它就是错的);话语还提供了一种对“底层”虚假的关心,“底层”也必须信以为真。新一代欧洲导演还是能够令人期待的。
《音乐》对“俄狄浦斯王”的解读
“柏林电影学派”主将安格拉·夏娜莱克的《音乐》是这次影展最重要、也最值得期待的影片。这部影片有一个“潜文本”,即《俄狄浦斯王》。作为欧洲文学最重要的IP之一,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故事有无数的演绎版本。夏娜莱克的电影显然与德国著名诗人荷尔德林的译本相关。这个译本对德国文化思想史有很大影响。就像翻译中常见的那样,荷尔德林译本有一些“误译”。但更为重要的是,他为此剧写下了很多注解。这些注解成为荷尔德林版本的解读,并在后来经黑格尔等人的诠释,使得“生就是死,死也是一种生”成为对俄狄浦斯的一种别致而深刻的理解。毕竟,假如弗洛伊德没有将俄狄浦斯用于精神分析,在恋母情结上大做文章,我们或许对这个形象会有全然不同的认识。
荷尔德林反对浪漫派诗人的“感伤的诗”,他认为古希腊诗人那里有一种稳固的东西,而悲剧的传递就是为了让它呈现出来。俄狄浦斯代表一种对信仰的终极追寻: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弑父娶母。这是最大程度的撕裂,是极限。而在临界状态中,他成为了母亲孩子的新父亲,因此获得了对时间和空间的新认识,感悟了终极哲理。这种通过死亡获得的大彻大悟,用黑格尔的话说就是“对于他自己和我们而言,都显得是在他的个性和人格本身中达成的和解”。换言之,这不仅是讲一个人的悲剧,更是在说一种存在的意义,即后来海德格尔所谓“向死而生”的意义。
这样理解一部电影是否有“过度诠释”之嫌?笔者认为,尽管不能一概而论,但了解相关的思想文化背景,对于理解欧洲电影来说是非常有必要的。否则,这里的影像就容易被错误理解为一种因为导演缺少艺术结构能力而导致的松散、逻辑混乱,即坊间似是而非的“意识流”,就像很多伪文艺片那样。
《音乐》不是一部容易“看懂”的电影,但并不是一部没有情节的电影。相反,它有一条精心设计的情节线索。显然导演让我们感觉到情节是在希腊展开的:在一种地中海氛围感的山海雾霭中,搜救队找到了一个灾难中幸存的婴孩,镜头让我们看到养父母清洗着婴儿脚上的伤口(俄狄浦斯在希腊语中意思是“肿胀的脚”,后面受伤的脚的影像也一再出现)。婴儿长成为青年,一个民谣歌手。他在路上意外地杀死了自己的生父(因为父亲认出了他而激动地想亲吻他),在入狱服刑后又意外与自己的生母、一个女看守结合,并生下了女儿。后来女看守在偶然得知真相后自尽,歌手多年后与女儿生活在德国的大都市,但逐渐失明。
《音乐》是有“门槛”的电影。对于观众来说,需要有些电影学习的基础才能“进入”到这部影片。夏娜莱克从走上导演之路伊始就深受法国电影大师罗贝尔·布列松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双重的:既是手法上的——比如对戏剧性的拒斥,对声音的巧妙设计,对影像表现深度的传递,对白大幅度的俭省,对人体局部(特别是手、腿)的重视,对音乐和影像关系的深刻理解等等;同时也是思想上的——布列松被称作电影界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没有争议的,这意味着手法直接服务于思想的呈现。
《音乐》的视听语言是非常丰富的。限于篇幅,我们仅仅举一两个例子。影片中男女主人公年龄跨度实际上不小,但是他们的样子几乎没什么变化,一直很年轻。如果我们回到荷尔德林式的俄狄浦斯,或许可以理解为这本来就是一个要去超越时间和空间之外的版本。影片中,监狱的看守都是女性,而且她们都穿着日式的木屐。这种不合理(常规的狱警当然要能够迅速移动)正说明了作为女性要承担的更多的苦难(也只有女导演会如此表达),以及本来在这里就不是警察机器的意义。女性对苦难有更为敏锐的感知,也承受了更多的苦。影片中的男主人公没有像俄狄浦斯那样自毁双眼,而是在自然的等待中逐渐沉入黑夜,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他逐渐获得了对生命更多的感悟和认知。
若想承担存在之苦难,就要终结一种怨恨的轮回、循环。而音乐正是这个过程的必需品。音乐能让苦难变得没那么苦。对于真正的人文主义者来说,禁止音乐是无法想象的。主人公民谣歌手的身份,正相当于古希腊—中世纪的“游吟诗人”。整个电影就是一部动人的复调音乐:维瓦尔第的美声歌曲、马尔蒂尼《爱的喜悦》、当代加拿大民谣,如同一部主题音乐的几个不同的声部——这几个声部看似不同,却和谐共鸣、回旋,令人低徊不已。这也是“复调”的真谛。《音乐》是作为电影艺术家的夏娜莱克送给这个充满不可知因素的世界的一份真诚的礼物——它不是阴郁的,而是一种“和光同尘”(尽管并不是老子的那个意思)。